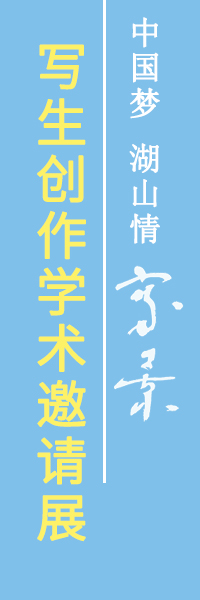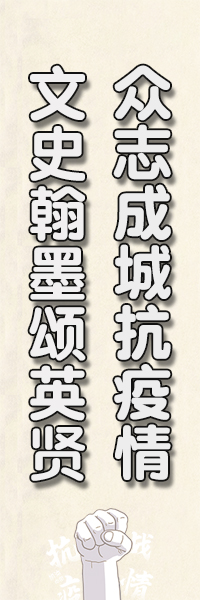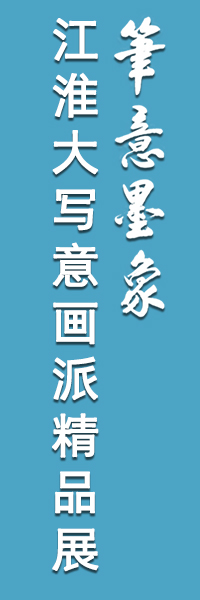融合創(chuàng)演“絲路奇幻秀”節(jié)目中融合了敦煌風(fēng)格的“新中式”時(shí)裝作品 賈璽增設(shè)計(jì) 圖片為作者供圖
【藝點(diǎn)】
“新中式”是近幾年建筑、家居、美妝、服飾、游戲、影視、動(dòng)漫等領(lǐng)域炙手可熱的關(guān)鍵詞。這種設(shè)計(jì)風(fēng)格的出現(xiàn)既非轉(zhuǎn)瞬即逝的時(shí)尚潮流,亦非對(duì)傳統(tǒng)的機(jī)械復(fù)制或?qū)ξ鞣皆O(shè)計(jì)的盲目模仿,它根植于中華文化的傳統(tǒng)哲學(xué)思想和美學(xué)精神內(nèi)核,立足于當(dāng)代生活方式和時(shí)代審美。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通過(guò)對(duì)水墨、戲劇、壁畫(huà)、榫卯等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元素進(jìn)行創(chuàng)新轉(zhuǎn)化,逐漸形成兼具民族特色、人文底蘊(yùn)、當(dāng)代審美與實(shí)用功能的美學(xué)體系。
差異化的設(shè)計(jì)風(fēng)格
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與“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同源異形,二者均根植于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,但前者通過(guò)現(xiàn)代設(shè)計(jì)語(yǔ)言對(duì)傳統(tǒng)元素進(jìn)行解構(gòu)與重構(gòu),形成兼具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內(nèi)涵與當(dāng)代審美的創(chuàng)新表達(dá),后者則更關(guān)注對(duì)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歷史形制、美學(xué)范式與匠作技藝的完整復(fù)刻。
在大力弘揚(yáng)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語(yǔ)境下,新中式、國(guó)潮與國(guó)風(fēng)構(gòu)成了傳統(tǒng)美學(xué)現(xiàn)代演繹的三種形式。三者雖然都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的體現(xiàn),卻在轉(zhuǎn)化路徑、表現(xiàn)形態(tài)與社會(huì)功能上呈現(xiàn)出明顯的差異性特征:“新中式”立足于“器物”的現(xiàn)代化改造,追求“藏”的克制表達(dá),實(shí)現(xiàn)傳統(tǒng)形式與現(xiàn)代生活的有機(jī)融合;“國(guó)潮”強(qiáng)調(diào)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符號(hào)的商業(yè)化再造,如漢字解構(gòu)、圖騰重組,強(qiáng)調(diào)“顯性”的符號(hào)拼接、視覺(jué)沖擊力,以及年輕化表達(dá)的消費(fèi)符號(hào)體系和消費(fèi)認(rèn)同感;“國(guó)風(fēng)”專注于“東方意境”的審美傳達(dá),通過(guò)詩(shī)性敘事(如影視中的水墨轉(zhuǎn)場(chǎng))呈現(xiàn)含蓄雋永的東方美學(xué)風(fēng)格。
傳統(tǒng)文化的現(xiàn)代表達(dá)
“新中式”本質(zhì)上是對(duì)經(jīng)濟(jì)全球化語(yǔ)境下文化趨于同質(zhì)化風(fēng)險(xiǎn)的反思,其核心價(jià)值在于建立傳統(tǒng)文化元素與現(xiàn)代生活的對(duì)話機(jī)制。它通過(guò)本土設(shè)計(jì)話語(yǔ)的自覺(jué)建構(gòu),即傳統(tǒng)文化的現(xiàn)代表達(dá),避免傳統(tǒng)文化的符號(hào)挪用和文化傳播中“失語(yǔ)”的情況,最終形成具有國(guó)際辨識(shí)度的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設(shè)計(jì)語(yǔ)言。從設(shè)計(jì)方法論角度來(lái)看,以筆者多年研究和從事的染織服裝設(shè)計(jì)領(lǐng)域?yàn)槔笾驴梢苑譃槲鍌€(gè)層面:
其一,傳統(tǒng)文化的當(dāng)代轉(zhuǎn)譯。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的理念在于,來(lái)自傳統(tǒng)又不拘泥于傳統(tǒng),而是立足當(dāng)代生活需要,通過(guò)不斷吸收流行時(shí)尚元素,借鑒現(xiàn)代藝術(shù)的表現(xiàn)手法,將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有效融合。例如,筆者曾以“敦煌·繁花”為主題,為陜西廣播電視臺(tái)“2024絲路春晚”設(shè)計(jì)一場(chǎng)新中式時(shí)裝秀,其中巧妙融合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服飾元素與敦煌壁畫(huà)的色彩和紋樣,既古典大氣又富有現(xiàn)代感。再如,某國(guó)產(chǎn)服裝品牌從傳統(tǒng)的“布盡其用”智慧中獲取靈感,通過(guò)對(duì)庫(kù)存零散面料的再利用,借鑒傳統(tǒng)“百衲衣”的拼布智慧,采用零浪費(fèi)剪裁工藝,化零為整、化古為新,使服裝既時(shí)尚活潑,又充滿質(zhì)樸的民間風(fēng)情。
其二,造型結(jié)構(gòu)的現(xiàn)代詮釋。“新中式”服裝設(shè)計(jì)在款式上突破了傳統(tǒng)服裝的式樣,以更多樣的時(shí)裝語(yǔ)言和造型觀念進(jìn)行設(shè)計(jì),強(qiáng)調(diào)“意在流褶”“疊穿層次”與“虛實(shí)共生”三大核心原則。意在流褶,是指具有流動(dòng)感的線性結(jié)構(gòu)與動(dòng)態(tài)平衡。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服裝一般為二維平面結(jié)構(gòu),講究肥碩寬大之美,既有自然垂墜形成的褶皺,也有精心制作的褶紋,比如現(xiàn)今流行的馬面裙上對(duì)稱排列、整齊有序的“馬面褶”。“新中式”服裝設(shè)計(jì)既注重“意在流褶”的東方韻味,又融合西方三維立體裁剪的造型方法,因此呈現(xiàn)出一種當(dāng)代美學(xué)特征。疊穿層次,是受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服飾“交領(lǐng)右衽”和“上下一體制”服裝文化的啟發(fā),強(qiáng)調(diào)衣襟、袖口、衣擺等部位的縱深感和層次性。虛實(shí)共生,來(lái)源于道家“有無(wú)相生”的哲學(xué)觀,強(qiáng)調(diào)通過(guò)視覺(jué)留白、結(jié)構(gòu)層次、面料對(duì)比等手法,營(yíng)造含蓄而富有張力的意境。比如某些服裝使用紗、羅、綃面料,巧妙融合中國(guó)水墨的通透韻味和不確定性,面料的“實(shí)”與水墨暈染的“虛”共同構(gòu)成一種靈動(dòng)飄逸的美感;還有些服裝外層采用傳統(tǒng)蠶絲薄紗或鏤空面紗,內(nèi)搭立體裁剪裙衫,形成“藏中帶露”的朦朧美感。
其三,新老材料工藝的碰撞融合。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重視絲綢、苧麻、香云紗等傳統(tǒng)材料與玻璃纖維、金屬紗、再生滌綸等現(xiàn)代材料的復(fù)合運(yùn)用,以及生物基材料(竹纖維復(fù)合材料)、智能材料與傳統(tǒng)工藝的結(jié)合,既保留傳統(tǒng)文化基因,又賦予其當(dāng)代生命力。比如,近年來(lái)“宋錦新中式外套”在時(shí)尚領(lǐng)域備受關(guān)注,一些面料廠家和時(shí)裝設(shè)計(jì)師不僅致力于表現(xiàn)“一寸宋錦一寸金”的非遺工藝之美,還開(kāi)發(fā)出宋錦加彈工藝,在傳統(tǒng)絲線中加入具有彈性、適于織造的真絲氨綸包覆絲材料。這種基于加彈織造工藝的彈力宋錦面料,不僅具有質(zhì)地堅(jiān)柔、典雅富麗的特點(diǎn),還具備彈性織物易于穿著、便于打理等優(yōu)點(diǎn),可以用于更多時(shí)裝樣式的設(shè)計(jì)。
其四,色彩基因的與時(shí)俱進(jìn)。不同于西方化學(xué)層面的色彩體系,中國(guó)古人從自然中提取顏色,將其應(yīng)用于繪畫(huà)、瓷器、服飾、建筑、漆器等方方面面,形成“五行五色”“正色”“間色”等色彩觀念。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服裝色彩很少是刺眼的、飽和度極高的,而是崇尚經(jīng)過(guò)時(shí)間沉淀的柔和、雅致的中性色調(diào),如月白、竹青、黛色,以及層次豐富的“暈染色”等。例如,敦煌石窟壁畫(huà)中的米色、棕色、咖色、群青等色彩,常被運(yùn)用于現(xiàn)代服裝設(shè)計(jì)之中,呈現(xiàn)出端莊、沉穩(wěn)的氣質(zhì)。此外,當(dāng)代設(shè)計(jì)師還依據(jù)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不斷開(kāi)發(fā)出新的“中國(guó)色”。如筆者在與某國(guó)產(chǎn)時(shí)裝品牌合作的“世遺國(guó)色·流光成錦”項(xiàng)目中,通過(guò)對(duì)我國(guó)多個(gè)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中包含的色彩進(jìn)行提煉和發(fā)掘,形成一套全新的色彩體系——“九曲·彩陶赭”“紅河·梯田棕”“龍門(mén)·石窟灰”“西湖·天水碧”“皖南·黛瓦黑”,等等。將這些根植于中華大地的色彩,運(yùn)用于時(shí)裝產(chǎn)品的設(shè)計(jì)中,形成濃郁渾厚的中華色彩風(fēng)格。
其五,圖案美學(xué)的形意重構(gòu)。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的圖案核心在于通過(guò)提煉、解構(gòu)與重構(gòu)傳統(tǒng)符號(hào),形成兼具文化底蘊(yùn)與當(dāng)代審美的設(shè)計(jì)語(yǔ)言,如將窗欞紋簡(jiǎn)化為線性骨骼、將云紋提煉為流動(dòng)曲線。這種解構(gòu)過(guò)程保留了原始符號(hào)的文化識(shí)別特征,同時(shí)剝離了特定歷史時(shí)期的風(fēng)格限制。在文化意趣上,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的圖案追求“形簡(jiǎn)意豐”的美學(xué)境界。例如,筆者在2025年6月完成的“牡丹亭”新中式主題設(shè)計(jì),將牡丹、蝴蝶、園林窗欞傳統(tǒng)圖案相融合,采用絲綢織錦面料織造工藝,形成頗具當(dāng)代感的“新中式”時(shí)裝圖案。
確立東方設(shè)計(jì)坐標(biāo)
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體現(xiàn)了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傳承性和創(chuàng)新性的雙重特性,通過(guò)“隨時(shí)代、隨生活”的適應(yīng)性演變,構(gòu)建起既能滿足當(dāng)代人審美與功能需求,又保持文化主體性的設(shè)計(jì)體系。
如今,在經(jīng)濟(jì)全球化推動(dòng)下,國(guó)際流行時(shí)尚越來(lái)越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,因此,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更需要構(gòu)建具有辨識(shí)度的“語(yǔ)言符號(hào)”和“敘事語(yǔ)法”。當(dāng)然不難看到,當(dāng)前大量所謂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所面臨的核心問(wèn)題在于表層符號(hào)挪用與文化內(nèi)涵的缺失。未來(lái)的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應(yīng)超越文化符號(hào)的拼貼,轉(zhuǎn)向?qū)鹘y(tǒng)服飾結(jié)構(gòu)、材料特色及符號(hào)轉(zhuǎn)譯的深層次探索。設(shè)計(jì)師需要通過(guò)持續(xù)的文化深挖與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,實(shí)現(xiàn)從“風(fēng)格模仿”到“體系建構(gòu)”、從“形式借鑒”到“精神再生”的跨越,最終形成既能回應(yīng)現(xiàn)代生活需求,又具有鮮明文化辨識(shí)度的設(shè)計(jì)范式。
“新中式”設(shè)計(jì)的最終目標(biāo)在于構(gòu)建具有當(dāng)代性的中國(guó)文化設(shè)計(jì)體系,實(shí)現(xiàn)從“中國(guó)元素”到“中國(guó)范式”的躍遷,為全球設(shè)計(jì)文明貢獻(xiàn)獨(dú)特的東方智慧。只有堅(jiān)持“守正”與“創(chuàng)新”的辯證發(fā)展,才能使中國(guó)設(shè)計(jì)真正實(shí)現(xiàn)從“中國(guó)元素運(yùn)用”到“審美體系建構(gòu)”的質(zhì)變,在全球設(shè)計(jì)文明格局中確立不可替代的東方坐標(biāo)。(作者:賈璽增,系清華大學(xué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副教授、博導(dǎo))
編輯:陳燁秋